从太平洋战争起因看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地位
作者:鹿锡俊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4期 时间:2025-08-28
讨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有必要再次确认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研究可从多方面进行,但如果以抗战时期的历史转折点为重点的话,我认为,澄清1941年12月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的起因,别具意义。从这个起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初相比,中国经过10年的浴血抗战,已经不是可以任意欺凌的国家,而是使日本深陷泥潭、不得不予以重视的国家。对反法西斯阵营来说,此时的中国也已经不是可以任意牺牲的国家,而是必须依靠也必须竭力支持的国家。因为,中国在东方主战场的抗战业已证明,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在保卫本国领土与主权,而且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而一些不愿正视历史事实的人,战后一直企图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推给美国、苏联与中国。他们的说法大致可概括为三类:第一,宣扬日美开战是因为罗斯福政府为有利于加入欧战而故意逼迫甚至引诱日本打响第一枪。第二,宣扬日本在德苏开战后本想北进攻苏,后因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阴谋”误导,才改为南进袭美。第三,宣扬美国在日美谈判的最后关头,曾经考虑过一个与日本的最终条件即“乙案”相似的“临时过渡办法”,后来因为中国国民政府坚决反对,才予以放弃;否则,如果美国正式提出该办法,日本就会放弃偷袭珍珠港计划,太平洋战争就可因此避免。
随着史料的开放及研究的深入,目前主张第一、第二类观点的声音虽然还存在,但不那么刺耳了。与此相反,宣扬第三类观点的声音却在变大。以日本右翼的一些论著为主,“中国对美国临时过渡办法的反对把美国拖入战争”“蒋介石与胡适挑起了日美战争”一类谬论沉渣泛起。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很多正视历史的学者虽然一直否定这种论调,但基本以“历史不讲如果”为理由,很少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辩驳。
由此可见,抗战胜利80年了,三个攸关战争责任的极其严肃的问题却还摆在我们面前:其一,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是否与日本的“乙案”相似,而具有让日本放弃偷袭珍珠港计划的效果?其二,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缘何拟议,又为何放弃?其三,日本对美开战是历史必然还是偶然?为了澄清谬误,本文着重围绕太平洋战争起因展开论述,力求对上述问题提出解答。
一、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是否与日本的“乙案”相似,而具有让日本放弃偷袭珍珠港计划的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比较一下日方“乙案”与美方“临时过渡办法”的异同,就不难得出结论。
1941年10月18日,以东条英机为首相、东乡茂德为外相的新内阁成立。遵照天皇“更广泛地研究内外情势,慎重思考”的指示,东条内阁连日举行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讨论应对日美谈判的最终方针。至11月1日,会议决定,一边继续对美谈判,一边在“开战的决心”下加紧备战,一旦谈判破裂即开战。与此相应,会议还就对美条件问题制定了由“甲案”和“乙案”组成的“不可再让的最终方案”。
“甲案”的宗旨是,对日美谈判中无法取得一致的三大问题——日本对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的态度问题、各国通商机会均等问题与日本在华驻兵问题,作出如下处理:第一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在形式上向美方靠拢,第三个问题则通过增设附加条件而继续坚持日方要求。按此宗旨,日本一边通过“甲案”表示可从中国撤兵,一边提出撤兵须在“日本与蒋介石政府的和谈成立,和平恢复之后”实施;而且,即使和平恢复以后,日本也须在华北、蒙疆、海南岛等要地继续驻兵,期限为25年左右。另外,日本一边表示可接受“各国在华通商机会均等”,一边又表示须在“全世界都适用此原则之后”才能落实。
“乙案”是东乡为应对“甲案”可能遭到美方拒绝而拟就的备案,最初内容为:(一)日美两国政府承诺不在法属印支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行使武力。(二)日美两国政府相互协作,确保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要物资。(三)美国承诺每年向日本供应100万吨航空汽油。正文之后的备选项是:(一)如果本协定成立,现在驻扎在法属印支南部的日军可以移驻法属印支北部。(二)根据需要,以往日本提案中关于无差别通商与日德意三国条约的解释及履行的规定可以追加。
但是,“乙案”内容遭到多数与会者强烈反对。理由是,它没有要求“美国停止援助中国”,故即使成立也将留下“祸根”。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通过的“乙案”除将东乡原案的第3条改为“日美两国政府相互恢复资金冻结前的通商状态,美国承诺向日本供应其需要的石油”外,特地增加了第4条,内容为“美国政府不得妨碍日中两国的和平努力”,实际含义则是“美国停止援助中国”。另外,备选项(一)改为:“如果本协定成立,可在必要时表明,日本有意在取得法国政府谅解之后,将目前驻扎在法属印支南部的日军移驻法属印支北部。另可约定,在中国事变获得解决,或者太平洋地区确立公正的和平以后,日本同意从法属印支撤军”。需要强调的是,因执意对美开战而期盼日美谈判破裂的日本军部之所以在最后同意“乙案”,是因为他们确信,只要有新增的第4条存在,美国就不可能接受,故日本最终可按既定方针对美开战。
11月5日,作为一系列会议的总结,日本再次举行御前会议,最终通过以上述11月1日联络会议各项决定为底本的第2次《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和《对美交涉要领》,并决定:日美谈判若至12月1日午前零时仍未成功,日本即发动对美、英、荷的战争。
日美谈判就这样进入最后关头。11月7日,日方向美方提出“甲案”,美方予以拒绝。按照既定步骤,日方接下来要向美方提交作为最终方案的“乙案”。但充当谈判代表的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认为,含有要求美方停止援助中国内容的“乙案”,比“甲案”更难获得美国同意,而日本现今因中日战争而精疲力竭,已无力挑起新的长期大战。基于这一认识,野村与另一位谈判代表来栖三郎未经东京同意即于11月18日向美方提出一份删除“美国停止援华”的第4条条款,仅以“日本从法属印支南部撤兵”交换“美国解除对日本资产的冻结令”。然而,东乡外相在接报后的11月20日痛斥野村,表示日本国内形势绝不允许此种交换,擅自提出此类条款,只会造成谈判破裂。同日,东乡再次强调“乙案”第4条的实质含义是“美国停止援蒋行为”后,训令野村按东京决定的内容向美方提交“乙案”。
华盛顿时间11月20日,野村遵照训令向美国提出“乙案”。不出野村所料,赫尔国务卿听完野村对“乙案”的说明后,对第4条“极显难色”,表示只要美国人民对日德意同盟条约抱有疑念,而日本亦不采取和平政策,美国就不可能停止援助中国。赫尔还强调,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与美国在华权益受到日本损害关系匪浅。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通过破译日本外务省密码而掌握了日本意图决裂的动向,为了赢得更多备战时间,曾考虑对日本提出一个为期3个月的提案,即前文提到的“临时过渡办法”。11月22日,赫尔就此向英国、澳大利亚、荷兰与中国驻美使节征求意见,并对中国大使胡适重申,日方要求美国停止援华,但美国自始即置之不理,“我等诸国,必仍继续援助中国之政策,以增固中国抗战能力”。24日下午,赫尔向英、澳、荷、中驻美使节通报了拟议中的“临时过渡办法”,大意为:日本承诺从法属印支南部撤兵,并将在法属印支全境驻军减少至7月26日前的兵力,总数不超过25000人,且不再增加;作为回报,美国允许稍微变通其对日冻结资产及限制出口贸易的条例。
对照美国拟议的“临时过渡办法”与日本的“乙案”,不难发现,尽管二者在日本从法属印支南部撤兵的问题上具有相似点,但在最关键的中国问题上则根本不同:日本的“乙案”以美国停止援华为绝对条件,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则完全排除此点。换言之,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与11月18日野村提出的私案较为接近,但如前所述,野村的私案早在11月20日就遭东乡完全否定。不仅如此,日方档案还表明,东乡于11月24日再次致电野村,强调日本所期待的并不只是恢复日美贸易与恢复冻结令前的状态,美国停止援华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条件,日本决不会作出比“乙案”更多的让步。
由上可见,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与日本的“乙案”存在重大对立,它即使不被放弃而最终正式对日提出,也必定因其逾越日本设定的开战红线而遭拒绝,其结果是,日军已经出动的舰队不会召回,偷袭珍珠港的行动不会中止,日本的对美开战仍将发生。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汲取历史教训,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历史事实,消除对历史的误解或曲解,否则就会陷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推卸责任的陷阱。
二、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缘何拟议,又为何放弃?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美国拟议“临时过渡办法”的目的。一些论著认为,美国之所以考虑“临时过渡办法”,目的是以牺牲中国而谋求对日妥协。这种看法并不符合1941年日美谈判后期的史实。现今能看到的各种原始史料表明,美国拟议“临时过渡办法”,并非企图以牺牲中国而谋求对日妥协,而是为了推迟日美战争爆发,以争取更多备战时间。这个目的是由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中国抗战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在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通过在欧洲援助苏联和英国抗击德国,防止以德日意三国为轴心的侵略势力进攻美洲,保卫美国的安全与利益。为此,在亚洲,美国既须阻止日本通过南进侵占英美的亚洲领地,以防止英国因丧失抗德资源而垮台;又须阻止日本实行北进而与德国夹击苏联,以防止苏联因两线作战而崩溃。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10年多的浴血奋战,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美国只有通过援助中国抗日,才能贯彻其全球战略,将日本困阻在中国战场,使其既不能南进,又不能北进。同时,美国则能够一边集中主要力量于欧洲,援助英、苏击败德国;一边增强在太平洋与亚洲的军备,最终解决日本问题。反之,美国如以牺牲中国向日本妥协,等于帮助日本解脱中国战场的束缚,助长日本南进或北进。
那么,美国为何最终放弃“临时过渡办法”呢?一些论著强调其原因在于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美国最终放弃“临时过渡办法”,系出于多方原因。首先,在赫尔向各国征求意见时,不仅中国强烈反对,其他各国对“临时过渡办法”也不抱好感,尤其是英国也以确保中国坚持抗战为主要理由,表明坚决的否定态度。其次,日本谈判代表野村与来栖也都指出,美方的最终态度与日本自身的四个错误密切相关:(一)日本的“乙案”要求美国停止援助中国,等于要求美国在德国坚持对外征服之际停止援助英国。对于致力于反对武力侵略政策的美国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二)日本“乙案”仅答应将驻在法属印支南部的日军移驻北部,意味着美国等国的兵力仍然被牵制在西南太平洋,故招致美国不满。(三)日本军政要人在国内继续鼓吹希特勒式的武力扩张政策,等于自我否定日本的和平意图。(四)对于如何应对“乙案”,英、荷、中等国驻美使节都须向国内请示,美国也须考量种种国内因素,日本却一味催促答复,导致美国感到遭受日本强迫。最后,美国自身情况也需重视。出于对中国抗日意义的高度认可,当时美国舆论的主流是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故“临时过渡办法”拟议的恢复对日供应石油等措施将遭到美国人民的广泛反对。另外,美国通过破译日本电报获知日本一边与美国谈判停战,一边秘密准备南进,激起了对日本背信弃义的愤怒。罗斯福等决策层由此认定日本响应“临时过渡办法”而放弃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极小,相反,“临时过渡办法”因遭到国内外的反对而造成的风险却极大。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最终放弃拟议中的“临时过渡办法”,于11月26日在提交日本的强硬照会中,全面拒绝了日本的所有无理要求。
总而言之,围绕“临时过渡办法”的波折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促使包括日本与美国在内的所有相关国家认清中国因素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日本才以美国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作为对美国的绝对要求,而美国也为维持中国抗战而拒绝日方要求。关于这个问题,重读一下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问答资料”中的观点,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它称: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使自己失掉了“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抗衡美国”、自由行动的弹性,这是日本的致命弱点。从长远来看,掌控中国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前提,而要保证中国听话,必须在其国土驻扎军队。因此,日美交涉的核心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核心是驻兵问题。日本对此绝对不能让步。
日本的这个自白说明,中国在东方主战场的抗战,其意义超出一国范畴,是对日本“北进”“南进”和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等侵略计划的最大阻碍,也是对美苏等国长远利益的重要保障,更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三、日本对美开战是历史必然还是偶然?
关于这个问题,不仅学界的既有研究,而且连日本当局的总结,都说明了1941年12月日本孤注一掷,对美开战,是其长期对外侵略的必然结果,而非偶然因素所致。理由很多,限于篇幅,在此先介绍一下1951年日本外务省在内部绝密文件《日本外交的错误》中提出的两个要点:第一,在对华政策基本理念、态度等问题上,日本始终没有改变错误,所以一切外交努力都是徒劳。“根本上错了,枝节上的苦心都不过是自慰而已。”作为证据,文件举例说,在1941年日美谈判的所有重大对立问题上,日本都毫无退让之心。尽管美国反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行径,日本却想让美国照单全收。如果日本真心开展谈判,本应作出实质性妥协,但其认为,美国因忙于在欧洲援助英法,无暇顾及东亚。押注于这一错误的判断,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始终拒绝妥协。第二,日本为推翻既存的国际条约与世界秩序,建立日本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选择与德国携手,丧失了理性,深陷于夸大与妄想之中,因而无法客观判断形势。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外交更是患上了“动脉硬化症”,拘泥于既往而无视现实,丢失了应有的柔软性、融通性与道义性。
最后,我想结合学界研究,再补充两点思考:
第一,与《日本外交的错误》自我揭示的缺陷相关,战时的日本当局虽然对本国的错误有所认识,但总体上将己方的纠错视为对中国的退让甚至施恩,故一边害怕中国因日本纠错而“得陇望蜀”,一边担心己方“退一步导致退百步”。这种心态所造成的心理障碍,致使日本不仅难以知错,而且即使知错也难以纠错,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譬如,1941年11月4日,在回答“既然对开战两年后的前景不明朗,为何还要对美开战”的提问时,东条英机强调,“从中日战争的角度来看,我若继续对美国日益加剧的经济封锁束手无策,必然对重庆与苏联造成影响,我在中国的占领地和满洲、台湾、朝鲜的向背亦会发生变化,结果我只能束手退回到从前的小日本去”。因此,与其对两年后的战局没有把握而束手待毙,不如趁有把握的两年“确保南方要地,奠定将来的胜利基础”。接着,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东条英机陈述了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连日讨论后得出的结论:美国对日条件的要害,是强迫日本接受实质是九国公约缩影的四项原则,我若容忍这些原则,“满洲国”将不复存在,日本与汪精卫政府所缔结的各种条约也皆有被废除的危险,日本还将无法统治像中国这样国防与资源上都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发言都露骨地点明了日本决策层决定孤注一掷对美开战的真实心态。
第二,历史表明,日本统治者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造成弥漫全国的狭隘的所谓爱国心以及对中国的鄙视和对英美的仇视。特别是在缔结日德意同盟条约后,日本民间大约有2000个从事国家主义运动的组织,其成员达63万人。伴随他们的活动而增长的普遍性的“对外强硬论”,反过来绑架了统治者,促使其因害怕遭受舆论反对而更加畏惧必要的妥协与纠错,从而明知没有胜算也拒绝悬崖勒马。
总而言之,关于“日本对美开战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答案包含的教训与启示是极为丰富的。如果说80多年前的历史给予日本的最大教训,是处理国际关系必须坚守理性,珍惜和平,立足长远的话,那么,在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升级的现状下,它对今日日本的启示,也许仍然是如何从根本上端正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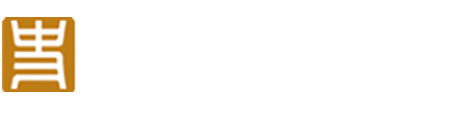
 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预约
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