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三项共识’、铸牢政治忠诚”主题征文|赵懿:马灯照山河——林伯渠的公仆人生
作者:赵懿 时间:2025-08-09
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静静矗立。灯柄的磨痕里,藏着1934年长征路上的风雪;灯罩的烟熏中,映着一位老党员74年的清贫岁月。这盏灯的主人,是被毛泽东誉为“公认的正派人”的林伯渠。
长征路上,林伯渠拄着竹拐杖,跟着中央纵队行军。组织配发的战马,他坚持用来驮运文件和伤员药品。警卫员看他腿伤未愈,牵马劝他:“部长,您上马吧。”老人拍拍马背的文件箱:“战士两条腿,我多了拐杖,算三条腿,够用了。”夹金山的雪夜,他的小马灯总在队伍最前,照亮冰裂缝隙,照见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草鞋。女战士李坚真回忆,每次过险路,老人总站在最暗处,举灯高呼“小心石头”,自己却摔得满身泥雪。
过草地时,警卫员偷偷留下缴获的暖瓶给首长泡药,林伯渠发现后急了:“送给卫生队,伤病员比我更需要。”这盏灯,不仅照亮了战士的归途,更在老虎沟救下坠崖的小战士——当谷底传来“看见小马灯了”的呼喊,他吊着绳索引路,用身体搭成人梯。
1937年冬至,边区政府为林伯渠新砌三孔石窑,他五次婉拒:“石窑留给伤员,土窑能听见延河说话。”土炕上,文件包当枕头,麻绳系裤带,断腿眼镜用草绳固定。斯诺采访时惊叹,这位边区主席的灰布衫补丁摞补丁,是伟大“东方魔力”的来源。
1944年大生产运动,他在机关门口贴出《个人节约计划》:戒纸烟、衣被自给、年交细粮两石。每天天未亮,他背箩筐拾粪的身影,总让农民张老汉心疼:“您留着粪肥自家地吧。”他却笑着摇头:“我这把老骨头,垦三亩荒没问题。”秋后南瓜丰收,他把四十斤重的南瓜籽晒干分给战士,自己仍用麻绳捆被头。警卫员偷塞新袜,他退回时裤管已磨破:“前线战士还光着脚呢。”
1941年,老红军肖玉璧贪污3050元公款,还倒卖边区物资给国民党。林伯渠连夜抱案卷见毛泽东:“贪污占比5%,不严惩,群众会寒心。”公审会上,面对肖玉璧“念在战功”的求饶,他签字的手青筋暴起:“边区没有特殊党员,贪半升粮也不行!”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指出,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纪律是党的生命,马虎不得。正是这种铁腕,让陕甘宁边区成为“最廉洁的政府”,老百姓交口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住在中南海漏雨的老房子里,管理局抬来新木料,他踩着摇梯阻拦:“加两根松木就行,别学故宫的琉璃瓦。”办公桌仍是延安的旧木箱,锁着1944年的南瓜籽和诗稿:“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对家人,他立下“三不”铁律:不写条子、不搞特殊、不躺功劳簿。1954年,侄孙虚报土改地亩,六封求情信均被退回,信封上“不理”二字力透纸背。女儿林利哭闹要吃小灶,他蹲下身:“大灶的小米粥,战士能喝,你也能。”儿子林用三从6岁起,就自己端碗去食堂排队,与战士同食粗饭。他常说:“高干子弟的特权,是党和人民的敌人。”
1960年临终前,林伯渠的铁皮箱里仅有:补丁灰布衫(毛泽东1937年所赠)、磨秃的钢笔、断腿眼镜。女儿林秉佑记得,父亲最后叮嘱:“做什么都要靠自己奋斗。”延河纪念馆的马灯前,讲解员总说:“这灯芯上的灰,是长征的印记。”
从瑞金到延安,从陕甘宁到中南海,林伯渠用马灯照亮他人,以拐杖丈量初心。他的日记里,没有半句豪言壮语,只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的平实承诺。74年革命生涯,他把“人民”二字刻进骨头,让廉洁之光穿越时空,成为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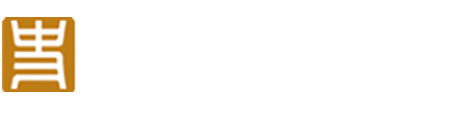
 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预约
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