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的空间生产与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以先秦秦汉时期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李磊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时间:2025-03-11
自中华文明进入国家阶段之后,伴随着统治机构的设立与疆域意识的形成,边疆成为一个既有别于内地、又有别于域外的空间。姚大力先生认为:“中国的边疆概念,要到晚清方才逐渐成熟,是指在一个规模远大于华夏、又小于‘天下’的‘中国’与其四邻界分判然之后,才会因中国境内有别于府县所辖之华夏的‘边裔’与国界以外的‘边裔’之间的归属区别而突显出来。”基于这一理论分梳,边疆学研究的对象以晚清为界,分为传统国家时期与现代国家时期这两种类型。本文所讨论的对象,即为现代国家观念出现之前传统中国的边疆。
对于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当代学者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参照予以阐释,将之称为“天下”国家、王朝国家,这为解读传统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分析框架。这些研究的理论关怀在于整全性与中心性,从边疆视野出发的论述,恰可与之相向而行,深化对传统中国的理解。近来学术界引入空间思维,从边疆空间性叙述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这不仅为边疆研究赋予了新的活力,而且将边疆的空间意义上升至中国的国家建构层面,对于建构中国史的学术话语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空间理论的引介,又为对边疆空间性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径。按照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理解,当社会关系纳入空间之后,空间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产关系,还是政治工具。空间具有三元辩证法,它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情感空间的统一。总之,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理论界的新进展提示边疆研究可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借助空间生产的视角来考察边疆的关系要素及其综合作用,并将之置于中国建构的宏大叙事中阐述其存在意义。这一探索以传统中国为主体视野,或许可以为中国史与边疆史的话语实践提供具有公共性的论述场域。
一、三代之政与边疆空间生产机制的形成
通常认为,疆域观念是战国变法的产物。随着郡县制、官僚制的设立,行政区划与治理权有了较为确定的区域范围,战国诸国也就演变为疆域型国家。在这一背景下,区分疆域内外的边疆也便随之而出现。但近来有观点认为,夏商西周时期已经确立了广域国家的疆域形态,邑等聚落之间的地域受到王朝的关注,“疆”为直接统治区,“略”则为统治的盈缩区。按照这一叙述,边疆观念的形成时间将进一步上推。边疆在以邑等聚落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中,便已经起着调整地缘关系的重要作用。
在传世文献中,尧舜禹及三代被描述为由九族、百姓、万邦构成的政治体。《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九族、百姓、万邦被纳入同一组织中,被置于不同圈层的位置上。《尚书》所描述的尧舜时期的政治结构,具有政治起源意义。商朝的统治建立在王族与各族之间统属、联盟与征服的关系之上。商朝灭亡后,周人以“族”为单位识别商朝遗民,在文献中留下“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的记载。西周分封制仍是以“族”为组织单元。《吕氏春秋·观世》云:“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这些数量庞大的“国”,有不少是“族”的形态。三代疆域的变化,是九族、百姓、万邦之间离合关系的变化。从空间角度来观察,作为疆域盈缩地带的边疆,正是九族、百姓、万邦的离合场所。
疆域形态的变化虽然是政治性的,但动力机制却是社会性的。先秦政治思想强调社会建设,注重利益平衡,将之视作立国之本。《论语·季氏》所说的“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着眼的便是分配正义,认为分配不均是国家倾覆的根源。在这一认识中,边疆危机被理解为内部凝聚力出现问题所致。《左传》“闵公二年”有关卫国覆灭的记载,便是这一治国要义的经典表述。卫懿公喜好鹤,甚至让鹤乘轩,这种将个人喜好凌驾于群体之上的做派遭到国人的非议。待到狄人攻伐卫国,卫懿公授予国人甲胄进行战争动员,结果遭到受甲者的拒绝。他们的理由是,鹤享有卫国禄位,它们才是卫懿公理当依赖的力量。由于失去国人的支持,卫军在荧泽之战中败于狄人。《左传》的叙事展现了春秋时期对于边疆危机的理解,认为内部凝聚力的丧失是边疆危机恶化的根本原因。
至晚在西周的治理思想中,维系社会的自我运行被视作国家的法度所在。国家力量既不能轻易施用于社会,也不能过度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周人在千亩被姜氏之戎所败,“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在边疆危机面前,周宣王试图通过由朝廷直接掌控人口以补充兵源和增加收入。此举遭到了仲山父的反对,他说:“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仲山父反对周王为了解决具有时效性的边疆危机而去破坏既存的组织形式。将料民视作“天之所恶”,表明时人将维系习俗与惯例视作天经地义之事。
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固然是决定国家强弱的重要因素,但它们只能按照习俗惯例提供,不能由国家强行征收。《孟子·滕文公》言:“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这一记述虽有理想化的一面,但对三代赋役进行规制化理解,表明孟子认为民众的责任是有限度的。责任的限度,以传统惯例为依据,而不能取决于当代执政者的意志。《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民是以能尊其贵……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刑鼎的铸造,意味着政治力量能够直达民众的个体层面,这将破坏既有的社会秩序,故而孔子认为晋国法度已失,难以长久。
三代之政之所以长期被视作典范政治,正在于所持的社会本位立场,边疆危机被视作是社会凝聚力丧失的结果,而疆域的扩大则是缘于德政的感召所致。《史记·五帝本纪》描述了虞舜之政对于四海之内的感召:“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在虞舜之政的感召下,边疆成为一个具有生产性的空间,不断容纳新的族群,并将之与内地对接。随着边疆族群的内地化,边疆又会发生地理推移,于是边疆由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演化为具有融合发展机制的社会空间。吸引边疆族群不断融入的,正是以社会为本位、注重分配正义的文明形态。边疆的空间生产,既是新的边疆空间的生产,也是中华文明在边疆空间中的再生产。
二、边郡:秦汉大一统在边疆空间中的呈现
以社会为本位的政治运行模式,在西周末期及春秋战国时期受到很大的挑战。随着竞争环境的逐渐恶化,周王朝及诸侯国越来越倾向于以打破惯例的方式汲取社会资源以度过政治危机。周宣王“料民于太原”开其先河,春秋争霸循其途径,战国变法蔚然成势。众所周知,战国变法的重要内容是推行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组织,并培育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基本的赋役单位。变法的思路是通过直接控制人力资源与田产等生产资料来增强国家能力。在变法过程中,三代之政中政治与社会的同构关系瓦解了。秦并六国之后,王朝利益进一步被推至极端。然而,孤悬于社会之上的王朝是脆弱的,在二世而亡的秦鉴之下,汉朝寻求协调政治统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避免二者出现极端性的对立。
在这一过程中,边疆逐步成为一个有别于内地的特殊区域。一方面,边疆在战国争霸及秦汉大一统战争中的军事功能越来越得到加强;另一方面,随着农牧分界线的形成,北方边疆成为具有不同经济形态与社会习俗的族群之间的往来场所,这种族群差异要超过三代之时。边疆性质的变化体现在行政区划层面,则是边郡的设置。《左传》“哀公二年”记载赵简子誓师时的许诺:“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郡的地位之所以低于县,乃是缘于郡是设在边疆地区,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而县则是或由灭亡的诸侯国改制而来,或者设在经济发达区,由国君任命官吏直接治理。战国时期的边郡,有些设置在战国群雄势力交错的地区,有些设置在邻接少数族群的地区。前者如秦国的汉中郡、南阳郡、东郡,赵国的上党郡。汉中郡在秦、楚之间,南阳郡在秦、魏、楚之间,东郡在秦、赵、魏、齐之间,上党郡则在韩、赵、秦之间。后者如楚国的黔中郡、巫郡,邻接西南少数族群地区。赵国的代郡、雁门郡、云中郡,燕国的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这些郡用以抵御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族群的袭扰。秦汉大一统后,原本设置在列国之间的诸郡,其边疆性消失。边郡主要设置于北方、西南地区,南方边郡则随着东瓯、闽越、南越相继融入大一统而逐渐内地化。至汉武帝时期,最终形成边郡、内郡的政治地理格局。
秦汉王朝用以维系边郡的人力资源很大部分为来自内郡的移民。秦始皇驱逐匈奴、夺取河南地,后又移民三万家于北河榆中地区,以移民戍守河套及邻近地区。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征匈奴,收复河套地区,汉武帝在此设置朔方郡。朔方的十多万移民为山东灾民。元狩四年(前119),汉朝在与匈奴的决战中获胜,汉武帝继续从山东迁徙贫民。《史记·平准书》云:“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从朔方到新秦中,汉武帝皆以官府的力量组织移民,并安排其生计。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除了将山东灾民、贫民迁徙到边郡外,汉武帝还让六十万塞卒在边郡屯田。
边郡的汉人人口主要来自内郡,他们大略可分为三类:一是移民,他们是边郡的常住人口,被编为编户齐民。二是朝廷委派的官吏与戍守边郡的军士。汉朝实行义务兵役制,成年男子须在京师或边郡戍守一年,虽然服役戍守的时间常常会超过这个期限,但戍卒仍然有机会重返内地,因而他们是边郡的政策性流动人口。三是内地犯罪的刑徒,他们被送往边郡屯田、戍守,修整城郭等设施,协助贫民耕作。
边郡实行与内郡相同的编户齐民制等国家基本制度,这使得边郡的社会关系与内郡基本一致。汉朝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既促成了内郡的经济繁荣,也促成了实行相同制度的边郡的社会发展。按照《汉书·匈奴传》所述,截至西汉末年,北方边郡的社会经济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朝的各项制度、文化、观念、人口等要素汇聚到边郡,这相当于将内地的社会关系移植到边疆的空间中去。
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国家基本制度及社会关系共同促进的结果,同时也是朝廷资源超常规投入的结果。《史记·平准书》言:“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司马迁记述了开通西南夷道、建设朔方的艰难。开通西南夷道的经费依靠“千里负担馈粮”、巴蜀租赋、征纳豪民耕田所得、朝廷的集资。建设朔方,则依靠整个山东地区的财政及漕运支持。可以说,西南、北方边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在全国财政的支持下完成的。
在安顿山东灾民及移民之时,汉朝朝廷承担了迁徙成本,如上引《史记·平准书》所言:“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县官”指汉朝天子。移民在边郡的生产资料也由朝廷安排,并派遣使者进行管理,“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这些生产资料中,除了农业生产资料外,也包括畜牧业生产资料。《史记·平准书》言:“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在适合畜牧业的边县,官府将种马借给牧民三年,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以此帮助牧民找到生计。
朝廷向边郡派遣官吏与戍卒,为边郡地区带来了组织管理者、劳动力及各种物资,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边郡行政机构与驻军的开支,主要由朝廷财政负担。元鼎六年(前111),斥塞卒六十万人在北方边郡戍田,“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六十万塞卒的粮食、兵器皆由朝廷财政承担。在南方及西南边郡,“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闲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在南方及西南十七个边郡初置之时,朝廷免除其赋税。为了维系边郡治安,朝廷征发南方吏卒,费用由朝廷与所经过的郡县共同负担。
边疆地区的建设消耗了汉朝的大量财政。汉武帝即位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闲,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闲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但设边郡及移民,“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边疆战事之后,汉朝财政更趋恶化,“于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可见边疆建设及其功能的发挥,绝非边郡自身力量所能完成,它是举国之力的结果。这与内郡除了完成自身的地方建设,还须向朝廷缴纳赋税的情况完全不同。不仅如此,边疆给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还迫使汉朝变革了治理模式。汉文帝时,朝廷接受晁错“入粟拜爵”的提议,鼓励富人买粟输往边郡,“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朝廷按照输送物资的多寡来授予向边疆转运物资者以不同等次的爵位,最高爵位可以达到大庶长。这是将朝廷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用作社会动员,将内郡的民力与民间财富用于边疆。汉武帝府库虚空后,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桑弘羊主持财政后,“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汉武帝的政治资源分为两种:一种是免税、赎罪、免除告缗、入仕为郎等特权,用以报酬贡献财富的商人及普通民众。一种是官秩、官职,用以奖励贡献财富的官吏。
除了用政治资源换取民间财富外,汉武帝还改革了经济管理方式,于元鼎四年(前113)取消郡国铸造钱币的权力,由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均输三官铸造钱币。制定盐、铁的专卖制度,在二十八个郡国的三十五处产盐地设置盐官,在四十个郡国的四十八处产铁地设置铁官,实行筦盐与筦铁。除了实行均输法、平准法外,汉武帝还以算缗、告缗的方式直接剥夺商贾财产。汉武帝的这些经济措施影响深远,成为后世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给边疆的用度。在这个意义上,边疆问题倒过来重塑了大一统的治理模式。
三、道、属国等特殊政区与秦汉边疆的接纳机制
秦汉边郡是大一统体制在边疆空间中的呈现。边郡除了汇聚内郡的各种制度、资源、观念之外,还由朝廷直接治理,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因而边郡的场域既具有与内郡相同的地方性,又具有大一统的整体性。从组织结构来观察,边郡实行与内郡一样的编户齐民制,以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基本赋税纳税单位,王朝不仅控制边郡的人力资源与田产、牲畜等生产资料,而且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调配到边郡以解决王朝层面的问题。在同时兼具地方性与中央性这一方面,边郡与内郡在性质上产生了区别。此外,三代之政中边疆对少数族群的接纳机制仍然发挥作用。如前所述,这一机制是以社会为本位、注重分配正义的德政(“天下明德”)来吸引边疆族群的不断融入。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由朝廷机构“属邦”管辖少数族群事务。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后,全国实行单一郡县制,北地义渠属北地郡,巴地蛮夷属巴郡,百越属会稽郡。少数族群隶属于郡县体制下的“道”,君长与部众皆要接受“道”的管理。在边郡下设“道”的体制被西汉所继承。根据《二年律令·秩律》,设置“道”较多的郡为北地郡、陇西郡、蜀郡、广汉郡,“道”中少数族群仍保留独立的社会组织。在秦汉制度中,少数族群不需要缴纳田租与承担徭役。汉初《蛮夷律》规定,设有君长的少数族群,其成年男子的义务是每年出一定数量的賨钱。有实证研究揭示,南郡夷道蛮夷,陇西郡、北地郡的戎狄均只需缴纳类似于“賨”的贡赋,便可免除徭役。由此可见,少数族群仍可在边郡中保留其社会组织,并且与编户齐民相比,所承担的赋税与徭役要少得多,这种治理方式正是对以社会为本位、注重分配正义之德政传统的继承。
边疆德政,同样用于绥抚新融入的少数族群。众所周知,匈奴的劫掠给边疆带来了巨大伤害,汉军与匈奴作战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汉武帝对待匈奴降人则采取了优待政策。《史记·平准书》载,“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这两处记载分别对应于元朔六年(前123)与元狩二年(前121)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之后,可知汉朝朝廷优待匈奴降人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政策。这两次对匈奴降人的安顿,均由朝廷出资。特别是为了供给浑邪王所率数万之众的衣食,汉武帝甚至省出自己的餐食车马费用,并打开私人库藏予以资助。相较之下,“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此战汉军虽胜,但战后不仅军队没有得到“转漕车甲之费”,战士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禄饷。对比对待匈奴降人的政策与对待有功将士的政策,可知汉朝在“财匮”背景下优先资助匈奴降人,这也是善待边疆族群之德政传统的延续。
接纳边疆少数族群之后,汉朝保留了他们的社会组织,设置“属国”这一特殊政区。元狩二年(前121),“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汉武帝将浑邪王所率的四万之众分为了五个属国。颜师古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可知匈奴人融入汉朝后其组织结构仍然留存,故而才有“存其国号”之意。此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五凤三年(前55)“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汉书·百官公卿表》:“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典属国为朝廷机构,属国都尉、丞、候、千人则掌管属国的具体事务。属国都尉的治所在边郡之内,依托边郡的行政资源与军事力量。按《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郡有属国都尉治满福,安定郡有属国都尉治三水,上郡有属国都尉治龟兹,西河郡有属国都尉治美稷,五原郡有属国都尉治蒱泽。属国保存了少数族群自身的组织,属国都尉的机构设置则连接了属国与朝廷及边郡之间的行政关系,这样既维护了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又保障了少数族群的组织完整性。可以说,属国一类的行政区划是边疆空间生产的重要环节,在以社会为本位、注重分配正义的德政原则下,它的设置不仅将治外的少数族群转化为治内的官民,而且将边外之地转化为境内之地,推动着边疆的空间移动。
除了属国等政区的设置之外,匈奴单于也被纳入汉朝的官爵体系中,这是边疆因素导致的制度变化。五凤四年(前54)“匈奴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甘露元年(前53)“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冬,匈奴单于遣弟左贤王来朝贺”。甘露二年(前52)“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对于呼韩邪单于的朝觐,汉宣帝以诏书的形式将其性质界定为“称北藩,朝正朔”。《汉书·宣帝纪》所载诏书云:“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汉书·萧望之传》载有同一份诏书,中有“赞谒称臣而不名”,可知在呼韩邪单于“称北藩臣”后,汉宣帝一方面“以客礼待之”,一方面又与之确立了君臣关系。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奉蕃称臣”,“三月,南单于遣子入侍”,二十六年(50)“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后汉书·南匈奴传》描述了南匈奴单于受诏的场景,“使者曰:‘单于当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双方不仅在文书制度层面,而且在礼仪层面确立了君臣关系,“单于”正式成为汉朝政治制度中的一个职位。《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了单于受诏后边疆地区的人口变化:
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北部边疆的八个边郡(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原来从内郡来的移民可以回归本土,由朝廷支付旅费与餐食。南下的匈奴则进入边郡,《晋书·北狄·匈奴传》记载:
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呼韩邪感汉恩,来朝,汉因留之,赐其邸舍,犹因本号,听称单于,岁给緜绢钱谷,有如列侯。子孙传袭,历代不绝。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
唐人修《晋书》,从长时段视角来回溯南匈奴的历史,认为南下进入并州北界的边郡,是匈奴人口滋生、分布广泛的重要缘起。在边郡之中,匈奴保留了部落组织,同时又被纳入东汉制度中“与编户大同”。尽管与编户齐民的制度身份相同,但匈奴民户却“不输贡赋”,受到了优待。匈奴进入边郡后的身份特征,反映了大一统时期边疆的空间生产功能:边疆是接纳少数族群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少数族群保留自身的组织,并受到优待;与此同时,少数族群在郡县化的边疆中又须完成身份的编户齐民化,与大一统体制相配合。
结 论
边疆问题是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代国家观念出现之前,传统中国的边疆发展遵循着自身的历史脉络。借用列斐伏尔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话语,传统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空间。所谓生产性是指边疆在国家建构、民族融合、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
边疆的空间生产性源起于中国早期的组织形态。在商周乃至更早的时期,政治与社会具有同构性,中国之所以走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道路,其根基便在于社会融合为政治认同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组织形态下,疆域盈缩其实是社群或族群离合关系的表现。边疆的价值在于为社会融合与政治接纳提供场所。以社会为本位、注重分配正义的治理思想是吸纳各个社群或族群融入中国的源动力。三代之政的治理逻辑,成为传统中国治边思想的起点。自此以后,注重内部社会建设以吸引远方族群的归心,成为传统中国处理边疆问题的宏远正道。
战国变法至秦汉制度建设,确立了以一夫一妻的家户为赋税单位的国家治理结构,由此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经由郡县制的设置,边疆成为政治体制层面的边郡。边郡实行与内郡相同的国家制度,汉朝的各项制度、文化、观念、人口等要素汇聚到边郡,这相当于将内地的社会关系移植到边疆的空间中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既促成了内郡的经济繁荣,也促成了实行相同制度的边郡的社会发展。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国家资源超常规投入的结果。汉王朝为边郡地区带来了组织管理者、劳动力及各种物资,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与内郡除了完成自身的地方建设还须向朝廷缴纳赋税的情况完全不同。正因如此,边疆问题会反作用于国家治理模式,促进制度变革的发生。汉武帝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缘于边疆给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可以说,边疆空间中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不仅仅作用于边疆,也作用于整个王朝。边疆在国家运行中具有枢纽的地位。
除了以编户齐民制度治理边郡之外,三代之政中边疆对少数族群的接纳机制仍然发挥作用,并且形成了制度规定。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由朝廷机构“属邦”管辖少数族群事务。在北地郡、陇西郡、蜀郡、广汉郡等边郡中设“道”,少数族群君长与部众皆要接受“道”的治理。在边郡下设“道”的治理体制被西汉所继承。借由“道”这一行政区划的设置,少数族群仍可在边郡中保留其社会组织,所承担的赋税与徭役远低于编户齐民。
除了“道”之外,“属国”这一特殊政区的设置也体现了同样的治理精神。接纳边疆少数族群之后,汉朝保存他们的社会组织,“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汉朝沿袭秦制,在朝廷设置典属国,此外还设置属国都尉、丞、候、千人掌管属国的具体事务。属国都尉的治所在边郡之内,依托边郡的行政资源与军事力量。“属国”的设置,既维护了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又保障了少数族群的组织完整性。“道”“属国”一类的行政区划是边疆空间生产的重要环节。在以社会为本位、注重分配正义的德政原则下,它的设置不仅将治外的少数族群转化为治内的官民,而且将边外之地转化为境内之地,推动着边疆的空间移动。
除了属国等政区的设置之外,西汉后期及东汉时期匈奴单于称臣促成汉朝的官爵体系的变动,“单于”成为汉朝政治制度中的一个职位。东汉时期,南匈奴南下进入边郡。汉朝一方面保留匈奴部落组织,另一方面又赋予其编户齐民的制度身份,“与编户大同”,并予以优待而“不输贡赋”。匈奴的身份变化,也反映了边疆的空间生产功能:边疆是少数族群的接纳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他们保留自身的组织,并受到优待,与此同时,少数族群在郡县化的边疆中又须完成身份的编户齐民化,以与建立在一夫一妻家户制基础上的大一统体制相配合。可见,即便到了秦汉大一统时期,以社会为本位、注重分配正义之德政传统,仍然是边疆所具空间生产能力的根由所在。
秦汉之后,历代王朝均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并延续了边疆治理思想。在传统中国,边疆既是关系要素的汇聚,也具有促进关系变动的能力。在边疆的空间中,同时代内地的观念、制度与物资在此汇聚,内地的社会关系也塑造着边疆的基本运行模式。但边疆的空间特性又不同于内地,它除了具有地方性之外,还具有国家性。国家的整体性在边疆空间中得到集中而具体的呈现,国家的目标、行为能力、责任义务也以边疆为重要的投射场域。边疆既叠加了地方性、国家性,还邻接着少数族群,成为他们进入中华文明的接纳空间。这多重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得边疆成为一个具有可能引发历史变动的场域,边疆空间由此便具有了生产“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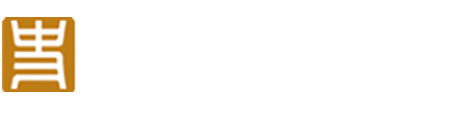
 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预约
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