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有的“采风”之说即与口述密切关联,在历代史书撰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发端后即蓬勃发展,毕竟现代社会中每个活生生的人都有权利留下自己的记忆和经历,给“那些在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发出更大声音的机会”,此即人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性的凸显,亦是尊重生命的体现,口述史则提供了一种可能与实践途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口述史面临更多挑战,包括真实性、规范性、过度实践等问题,故需要经过专业素养培训的口述实践。口述史“何去何从”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问题的解答已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文试图观察口述史本身的特性,从记忆史的角度回答其生存之道,及应如何进行自身定位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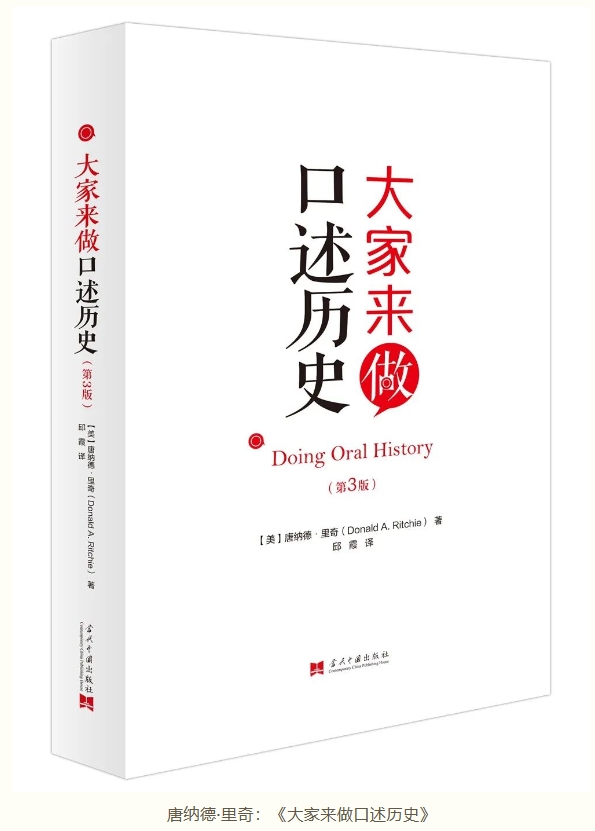
一、“生命记忆史”的提出
近年有学者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其要义是“关注生命”。史学要探究“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记忆史进入中国史学界以后,相关实证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记忆的原初理解,即人的记忆,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学术研究加深,诸如文化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记忆空间等新词应运而生,似与“人”逐渐游离。这些记忆本质上均应有“人”,才能显得鲜活并且生动。记忆史似可与生命史学勾联而成“生命记忆史”。
“生命记忆史”并非强调诸多记忆史研究中应该有“人”,而是一种专门的记忆指向,即生命记忆的实现与实践,每个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理应受到尊重,皆有留下生命记忆的权利与价值。“生命记忆史”强调“人的记忆”,其主体是生命个体,换言之即“人”。中国历史关于人的书写从未缺席,《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等,皆以人物为中心,但其所谓的人多为帝王将相,且属于被书写的对象,而非书写者,故传统史学体系下,“人的历史”或是重要内容,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更以提倡书写普通人的历史为要。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其个人指英雄,而群体指普通人组成的社会群体,故要求注意普通大众的历史。无论如何,这些观点尚停留于改变书写对象,书写者依然是历史学者或知识精英,换言之,仍未触及谁最有资格书写“生命记忆史”的根本问题。20世纪70年代,英国伦敦东区下层民众发起的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或能提供某些启示。他们主张社会民众直接参与口述史写作,使普通民众相信自己不仅可以利用该方法确立历史,也让他们相信自己有撰史能力,印证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史学已非史学家专利。这从根本上颠覆了史学研究的归属权问题。
“生命记忆史”的客体是个人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从宽泛意义而言,所有历史书写皆可归于记忆范畴,暂不论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强调的“人”非普通个人,其书写的内容更非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这导致人被平面化,仅留干瘪瘪的粗枝大叶。梁启超将之归为“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即“无其精神也”,所以“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当然,“生命记忆史”的书写并非只有自己才能完成,但对生命的认知、体验与表达的确只有自身才最具资格。或许当前流行的心态史学值得关注。彭卫说心态史学具有双重含义:“第一,方法论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上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第二,理论思维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理论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法,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心态史学的某些内容符合“生命记忆史”的部分目标,与之有重合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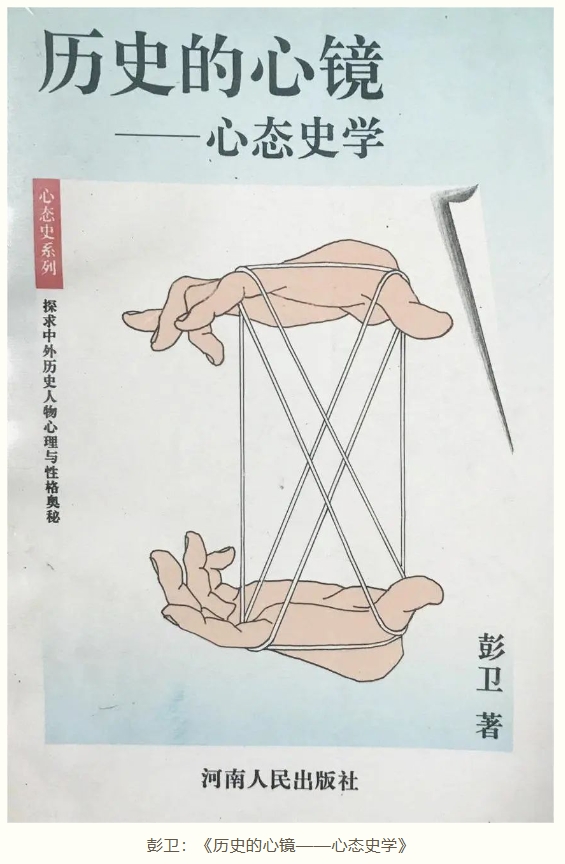
二、“生命记忆史”的实现途径
“生命记忆史”从本质上是记忆实践而非记忆研究,换言之,记忆实践不仅是“生命记忆史”的起点,亦是其内核。“生命记忆史”要求个人应留下记忆,能够关注到其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口述史为“生命记忆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口述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也是天然联盟,不存在没有记忆的口述。记忆为口述史的核心,而口述史的目的是收集记忆,体现出口述史的温情维度。某种程度上,历史往往以冷冰冰的面目出现,若掺杂太多情感、立场、情绪、态度,则难称“历史”。口述史是为数不多的使史学工作者还能与普通民众沟通交流的渠道。口述史通过记录访谈的形式收集他者记忆,该过程正是一场“心灵对话之旅”,使生命记忆得以保留。
当然,到底有多少人能真切感受口述史的魅力,该问题显然难以回答。毕竟现今从事口述史研究者,因各自目的与出发点有异,存在将之异化的嫌疑,本属知性温情之物变成了功利被迫之途。口述采访过程中,只有用心聆听感受正在口述的受访者,与之实现真正的心灵对话,才能达到口述的目的。若心不在焉,那就难以保证真正感受“口述”。现实中的口述采访,仅仅为了实现某些“目的”,难以让人产生温情之感。或许不应过分苛求口述史的理想状态,毕竟还有太多仍处于进程之中,无暇顾及原本的优雅和温情。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口述史对于“生命记忆史”的意义,则不得不从口述史的属性说起。
口述史具有生命属性。口述史的开展有赖于活生生的生命个体,难免予人“私属”之感,某种程度上表达的仅是个人记忆。诸多研究者也纷纷凸显口述史的如此特性,留下个人属性的深刻烙印。陈墨说“口述历史其实是采访人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道出了口述史的本质属性,确实只是某些个人观点和看法,或某些个人经历和生活。刘亚秋说:“口述史资料中凸显了生命或主体的形象。”如此观点将生命情感和尊重置于首位,强调口述是个人表述。“温情”或许是人文社会科学理应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意义之一,如何解决人活着的意义问题,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人的交往,如何对待生与死的到来,等等,可大可小的问题都牵涉“人何以为人”的终极命题。人类历史上不乏饱含智慧的答案,但也有不少随生命消逝而灰飞烟灭。口述史的理想追求是成为人类智慧的集合体,让每个人都能留下其“口述资料”,形成“人类个体记忆库”,让“生命记忆”的温情发挥至效。
口述史具有社会属性。口述史的社会属性,与生命属性并不对立。生命属性虽强调口述者的个体生命体验与个人记忆,但生命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体现其价值和意义。哈布瓦赫试图证明的“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故“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换言之,记忆必须有其社会基础,个人口述源于自身在群体中的位置确认。这里实际上涉及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个人口述并非空穴来风,所讲述的人生与故事均被置于社会或群体中才能获得意义,而个人生平口述史即“生命记忆史”的实践,本身即有语言、风俗、道德、认知、观感等迥异于动物属性的内容,此皆社会性的表现。
口述史具有实践属性。从口述史的概念或定义出发,实践属性指口述必须进行“记录访谈”,意味着应该有某种“行动”,而非仅仅停留于思考。口述史要求研究者踏踏实实地行动,往往还要求能说会道,与受访者保持良好互动和关系,留下不错印象,才能使之“敞开胸怀”畅所欲言。实践属性还指口述史讲究技巧训练与规范化操作。唐纳德·里奇呼吁“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强调“大多数口述历史学家是通过实践来学习的,我们对访谈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往往是滞后于而不是超前于访谈实践的”,所以,他还“附录”“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关于口述历史的原则和最佳实务规范”。左玉河亦特别强调口述史的规范化,认为必须制定一套通行标准,才能弥补和纠正口述史研究过程中的诸多随意行为。但这些皆非对技巧培训的标榜,而是凸显访谈技巧的训练与成熟有赖于口述实践。
口述是个体生命记忆的诠释,但口述史落脚于社会层面,不仅口述唤醒的记忆源于社会,且口述史是一项社会实践工作。概言之,口述史尤其是个人生平口述史是个人生命记忆的社会实践,这恰恰是“生命记忆史”的实现。

三、“生命记忆史”的出路
个体生命记忆的脆弱不言而喻,口述作为个人生命记忆的表达,时刻面临被遗忘、移植、筛选等挑战。口述史固然要求唤起受访者回忆,使记忆更连贯,似乎也可以让历史更清晰。但真正具有贡献意义的是,要解决“我们应该记住什么,我们可以忘记什么,我们必须忘记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口述史更具价值。就目前而言,口述史的重要目的在于保存记忆,尤其是某些受访者或出于某些原因导致选择性记忆,或对某些事件出现遗忘,这时采访者往往会选择“刺激”或“交心”以求能获取记忆。我们应该质问,这些记忆是属于受访者?或仅为采访者内心所需?采访者为了能收获自己所需要的记忆而有不择手段的权利?得到的生命记忆或许本即受访者内心预设,仅为求得印证而已。
当我们重视个体生命记忆时,有没有思考过受访者与遗忘的关系,那些或许经历万般痛苦的口述受访者,当他不愿意回忆,或因过于痛苦而选择性遗忘时,是否应该受到尊重?这些牵扯到记忆的道德问题,也正是当今口述史面临的重要挑战。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在阐述“共享记忆工程”时,即相当明确地肯定“最有希望的共享记忆工程是那些自然长成的记忆共同体,可以说,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对待来自历史的痛苦的创伤记忆”,并指出“需要甄别的问题是人类应当记住什么,而不是记住什么是对人类有利的。在守卫道德和提升道德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提升道德是一种较高的愿望,守卫道德则是一种必需”。有些个体生命记忆可能消失,且有其消失的理由与正当性,这个时候口述的正义感何在?不能仅仅是为了保存个人生命记忆这个理由。换言之,个体生命有忘记的权利,但是没有记住的义务。虽然全体人类记忆工程具有理想上的完美,但记忆遭遇遗忘、筛选等均属常态,也不可能留存纯粹的没有任何遗忘与筛选的记忆。在该意义上,口述也面临如何处置与对待个体生命记忆的挑战。
口述史在书写过程中还面临其他挑战,如口述记忆的竞争。个体生命记忆固然重要,但也存在一些相当明显的竞争可能。个人在事件中的立场、地位,个人的知识背景、成长环境,以及诸多因素皆可能使不同个人的记忆存在竞争。这可归纳为“权力”影响记忆,此处指泛化的权力。当面对竞争时,应遵循怎样的原则以辨别真伪?甚至也有人会质疑,记忆果真有真伪之别?其实,这里涉及的是遗忘与“谎言”应被如何对待的问题。遗忘的问题前面已有所回答。口述史中的谎言应被如何处理,这在口述史研究中可被当作一门单独的学问,乃至成为一个“学科”,涉及心理、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常言道,“谎言也是真相”,这或许是口述史研究中如何对待谎言的最佳答案,但同时也可以说这句话是简化乃至敷衍。谎言的产生应该追寻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即权力如何影响谎言。
本身充满温度的口述史在这些挑战面前易乱阵脚,从而引发“何去何从”的追问。个体生命记忆实践与谎言虚假信息的矛盾难以调和,但真实性追寻的难度或困境并不能给口述史不作为提供任何借口。口述史更应迎难而上,尽可能地保存个体生命记忆以提供其力所能及的人类智慧。
人类记忆的保存使口述史的意义、性质、功能和价值得以凸显。口述史的生存之道,即起到传承记忆的作用。从实质而言,口述史即采访者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离开记忆谈口述史难免造成空泛。从该种意义上而言,口述史属于个体生命记忆的实践,但若仅停留于此,则在陈墨所言的人类记忆库建成之前,随时皆有被抹杀的可能。更何况,人类记忆库除技术层面的难题外,将面临更多伦理方面的困境,突破与处理之难,层层“权力”的牵扯更是将那些原本已形成且愿意公开的个人生命记忆化为灰烬。如今口述史要解决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并非深度挖掘那些尚未被人知晓的个体生命记忆,而是如何保存已经获取的个人口述,使之得到传承。
口述史中有属于个人生命记忆实践的部分,而文化记忆目前作为相当流行的记忆理论,其面向为这部分个人生命记忆的保存与未来提供了相当启发。作为个体生命记忆实践的口述史,在走向建构文化记忆的道路上尚有不少荆棘,但这也正是未来口述史的生存之道。阿莱达·阿斯曼在用“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作为副标题诠释“记忆中的历史”,似能帮助理解个人生命记忆型口述史何去何从的问题,阿斯曼的“公共演示”即“文化记忆”的存在方式,个人生命记忆实践型的口述史是否也能以“文化记忆”的方式存在,从而得以保存和传承?文化记忆虽然也有被抹杀、篡改的可能,但相较之下却更利于保存与传递,也更能体现其价值和意义。
“生命记忆史”的原初形态属个体生命记忆实践,但这些记忆稍纵即逝,只有文化记忆才能稳定个体生命记忆。个体记忆对于自身而言相当重要,是自己身份的建构基础。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这些记忆是“经验、关系以及自己身份感觉得以建构的材料,但是我们自己的记忆中只有很少一部分通过语言得到处理,并明确形成了我们生命故事的背景”,其中大部分记忆皆处于沉睡之中,需要“被外界因素唤醒,在被唤醒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因此,口述史操作作为主动措施,在唤醒个体生命记忆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口述史的本意即要求唤醒被采访者的记忆,但是这些个体生命记忆存在碎片化、流动性等特点,也不连贯。
个体生命记忆作为口述史研究成果,若非将之转换成“文化记忆”,只能停留于被束缚的过去。个体生命记忆应有明确目的和指向,或存于图书馆或档案馆,或用于教学或博物馆展示,或呈现于戏剧表演或互动视频。但不管如何,这些皆属“公开展示”,亦即将用于社会实践。所以,那些随意或暗中的录音,那些窃听或私人录音日记,那些没有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的录音,皆不能归于口述史范畴。
文化记忆需要物质载体,具有跨代性特点,若非意外能无限延续,文化记忆化即将短暂之物转化成永久之物。阿莱达·阿斯曼说:“虽然活生生的记忆随着记忆者的死去而消失,但是文化的物质遗存通过机构——他们使得活生生的记忆超越了其原初语境——有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当它们被放置在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地方的时候,它们就获得了永久性保存的机会。”这仅仅是关于文化记忆的较为抽象的描述,实际上,文化记忆的获取往往属于象征与符号性,且其个体记忆在其中的作用亦不容忽视,没有个体记忆的展示很难有文化记忆的丰富。个体生命记忆只有文化记忆化,才能得到长期保存,才能产生积极意义。口述史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使个体生命记忆得以表达和公布,但是否能成为文化记忆,则需要正规化操作与事后恰当处置。
口述史有一套完整的规范的操作程序,只有严格遵循,才能使个体生命记忆得到尊重,实现其价值,赢得其地位。这些在口述史学科内有较多讨论,包括如何进行个人口述、如何进行问题设置、如何处理谎言问题等,均影响到个体生命记忆能否有效成为文化记忆。故活生生的记忆通过口述采访者的操作,有望得到妥善保存,从全人类生命记忆而言,使之皆成为“文化记忆”显然不太可能,但就某些具体个人而言,则有望通过个人生平口述,使其记忆获得永久性保存机会。文化记忆应该是个体生命记忆的最佳归宿,其实现却面临重重挑战。
“生命记忆史”提出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都应该得到尊重,皆有留下记忆的义务和权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因此,个体生命都应该通过口述史留下属于个人的生命记忆,并通过文化记忆化得到永久保存的机会。如此才是人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性的凸显,展现个体价值,亦是现代社会的温情所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之道。

(作者郭辉,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