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割据政权长期并立、分庭抗礼的历史阶段,也是诸政权及其辖域民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内聚,逐渐从各自称“中国”发展到共奉“中国”之号的历史时期。
各政权正是在尊孔崇儒的基础上,共同继承了隋唐五代以降华夏的官僚、科举、行政、律法——即“中国之制”,从而自然而然地共奉“中国”之号,由此孕育出“大一统”的因素,为元明清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自称“中国”与炎黄认同
公元10—13世纪,随着五代时期各政权间的频繁互动,以及唐以降儒家“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互化思想在周边的迅速传播,诸政权逐渐挣脱“中原政权即中国”的束缚,开始自称“中国”并自认正统。
契丹人据有幽云地区后,逐步自称“中国”,以华夏为正统。辽朝的《鲜演大师墓碑》就有“大辽中国”的说法。
不仅如此,辽还以“炎黄子孙”的身份接续至“中国”的谱系。1009年,《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称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的祖先为轩辕黄帝八世孙虞舜后裔。1095年,《永清公主墓志》同样记有辽人为“轩辕黄帝之后”。而《辽史·世表》记载则有所不同,认定“辽之先,出自炎帝。”
无论如何,契丹人已认定自己为炎黄子孙。既然自称“中国”且系出炎黄,自然认为自己的政权就是华夏正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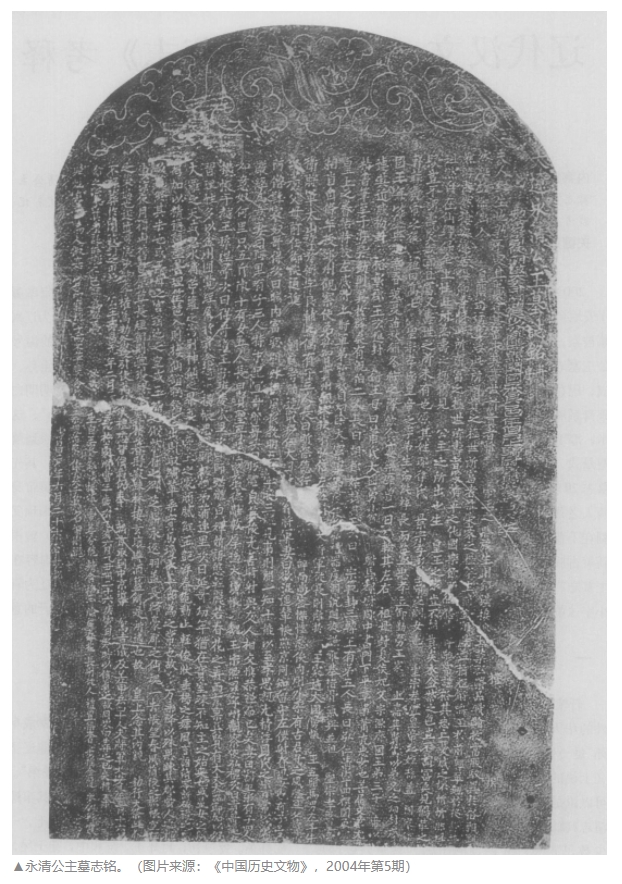
辽太宗入主中原后,从晋末帝手中获得“秦传国玺”,因而自认为“天子符瑞”尽归于辽,自然也就继承了华夏正统。辽圣宗为此还专作《传国玺诗》称赞此事,之后辽兴宗又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为题策试进士。
道宗册封高丽国王时更是说:“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体现了辽人正统意识的不断强化。
西夏人虽未自称“中国”,但自认为是华夏一脉,亦系炎黄子孙。李元昊立国后遣使向宋上表时,自称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并一度模仿孝文帝“改姓元氏”。而北魏的拓跋鲜卑自称为黄帝次子“昌意少子”之后,李元昊自称拓跋鲜卑之后,自然认为自己是黄帝后人。
金人据有中原后,便自称“中国”,且以正统自居。
章宗时,参知政事独吉思忠就防备韩侂胄北伐而谏言:“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此“中国”即指金朝。
金人甫一建国便诏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地位,诏书言:“辽政不纲,人神共弃”,故而“率大军以行讨伐”,是为“中外一统”。
此后,金朝君主也不断强调自己的华夏正统地位。海陵王谓“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世宗则直言:“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明确宣称金朝才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
共奉“中国”之号
北宋时,虽未见宋人称辽为“中国”,但辽宋之间互称“南北朝”,君主以一家之兄弟相称。
澶渊之盟后,辽宋双方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
辽宋互称“南北朝”,即“中国”之南北朝。所以辽兴宗直接就说辽宋“两朝事同一家”。辽道宗也明确说辽宋“虽境分二国……而义若一家”。很明显“一家”即“中国”,“南朝”是中国之南朝,“北朝”系中国的北朝,南北两朝皆为“中国”。

西夏建国前,宋太宗得党项绥、银、夏等州后,招诱这些地区的官吏与民众迁入宋境生活。面对此景,党项人的首领李继迁无奈地对其臣僚张浦说道:眼见“中国以财粟招抚流民,亲离众散”,却无能为力。显然,此时党项人认为宋朝即指“中国”。
李元昊建国后,不仅自认华夏一脉,而且欲与辽宋三分天下,“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朝)”,宋为南朝,认为辽宋夏当共奉“中国”之号。但在经过与辽、宋的数次战争后,西夏最终向辽、宋俯首称臣。然而,不管建国伊始要三分天下还是后来向辽、宋两国称臣,西夏一直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分子,从未脱离共奉“中国”之号的框架。
同一时期,由回鹘人建立的、地处今日新疆及中亚地区的喀喇汗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而且其君主自称桃花石汗(“中国”之汗)。在喀喇汗王朝的《突厥语大词典》中,“秦”即指中国,故它以“上秦”“中秦”“下秦”分指宋、契丹以及喀喇汗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显然表示宋、契丹、喀喇汗王朝共奉“中国”之号。
高昌、吐蕃、大理等政权,也以纳贡请封的方式共奉“中国”之号。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如公元965年、981年、983年三次进献方物于宋;981年向宋太宗上书时,更自称“西州外生(甥)”。吐蕃六谷部多次向宋进献马匹;唃厮啰亦多次纳贡于宋,并乞官职,又于公元1116年将辖域全归为宋朝郡县。大理多次遣使向宋请求册封,宋徽宗于1117年册封大理国国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可以说,辽宋夏金时期,诸多政权在自称“中国”、宣称继承华夏正统的同时,逐步完成了对彼此作为“中国”一分子的身份认同。
随着与中原王朝交往交流的深入,辽夏金政权逐渐接受并形成了共尊儒家文化的理念。在尊孔崇儒理念的影响下,辽夏金政权在官僚、科举、行政、律法四方面共承“中国之制”,从而完成了由自称“中国”到共奉“中国”之号的转变。
共尊儒家之道
宋朝继承了唐五代尊孔崇儒的理念,不仅在中原大兴文教,而且在西北、西南地区创设“蕃学”和地方文教机构,以此推行儒家思想。
公元918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身边侍臣应该先祭祀哪位“有大功德者”。侍臣皆认为应当敬佛。
辽太祖却说:“佛非中国教”。
太子耶律倍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辽太祖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兴建孔庙,并让其春秋释奠。由此奠定了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
西夏仁宗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并翻译儒家经典,以《孝经》《论语》等为教材,确立儒学在西夏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尊孔崇儒之风得以形成。
金熙宗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建孔庙,又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璠为衍圣公,还亲莅孔庙奠祭,并认为“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金代尊孔崇儒之风自此确立。

共承官僚之制
尊孔崇儒之风在辽夏金的确立,促进了各政权对隋唐五代各项“中国之制”的继承。
辽在拥有幽云农耕区域后,将农耕区域的州县制与契丹人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元制,并由此“官分南北”。南面官系统仿隋唐五代之制“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管理汉、渤海等农耕人口的事务;北面官系统“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这一“因俗而治”的二元制,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促进了辖域内的民族交融。

女真人早先实行勃极烈制(女真人实行的带有浓厚贵族议事会残余性质的朝官制度),金朝开国之初仍用旧制。随着辽宋降官的大量涌入,金太祖便模仿辽人旧制,设置长吏、枢密院,以此初立“汉官之制”。金太宗时设置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自此仿效中原农耕区域中央集权体制之法初具规模。至熙宗“天眷官制”改革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在此基础上,海陵王于1156年进行官制改革,“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使得中央集权体制更为完备。
共承科举之制
辽朝效法唐与五代官学之制,设国子学于上京与中京,置五京学于五京,在地方设府州县学,自上而下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
辽人在保留契丹世人选制的基础上,设置科举,以“唐宋之制取士”,分设甲、乙、丙三科。此举既保留了自身传统,又提拔了诸如刘六符、马人望等一批肱骨汉臣,加速了辽朝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西夏的科举之制并非一蹴而就。李元昊即位后便创建蕃学,“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虽然使用的是“蕃语”,但所学内容却是《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
金朝立国之初,太祖就注重中原文化,曾下诏攻克中京所获的礼乐仪仗、图书文籍,要首先运至他那里。自然,金朝十分重视儒学教育,“自京师至于郡邑,莫不有学,使秀民得以讲道艺其中”。
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金朝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设南北选。科举考试科目仿照辽宋,“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后来,海陵王增加殿试,合并南北选,只以词赋取士。世宗时,创女直进士科,称“策论进士”。章宗时,又增制举宏词科。
但不论金代科举制度如何变化,其主旨仍不外“合辽宋之法而润色之”。

共承行政之制
虽然辽已确立契丹人和汉人治理的二元制,但从辽朝历代君主为巩固自身权威的努力来看,部族制的因素被逐步消解,二元制逐渐向唐五代的中央集权制过渡。
辽人采纳唐五代的治理经验,建立起道、府、州、县等科层化中央集权管辖模式,在地方设五京、六府,一百五十余州、军、城和二百余县。这不仅使“人民皆入版籍,贡赋悉输内帑”,而且将原先辖域内部族制占主导的地区初步纳入中央管辖体系内。
之后,辽圣宗进一步将部族社会中最为典型的王公贵族的头下军州(辽朝的一种行政机构,其税收除酒税外概归本主所有),以直接籍没和间接收权的方式收归国有。
与之对应,圣宗还解放皇室斡鲁朵内隶宫州县的人口,以此变相削弱斡鲁朵的私有属性,为隶宫州县最后纳入国家版籍(登记户口、土地的簿册等)作好了准备。不仅如此,圣宗以奚王所献之地改建中京,一举解决了国中之国的问题。
这种二元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对辽整合中国北方功不可没。
西夏行政体制基本沿袭唐宋,设置府、州(郡)、县等,实行中央集权管辖模式。
金朝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由最初的猛安谋克制(金朝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组织,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向“以汉制治汉人”转化,并承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共计十九路。
概言之,金朝虽保留猛安谋克及部族、乣(辽、金、元时期对归降的北方各部族的统称)等特有政治军事组织,但路府州县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治组织形式始终居于主体地位。
共承律法之制
辽朝立国后仍用契丹人习惯法,如“射鬼箭”“没入瓦里”等刑名。
太祖时,“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此《律令》即指唐律令。此时,契丹习惯法与唐律令因蕃汉分治而并行。
太宗时,汉法开始适用于契丹人、奚人、汉人、渤海人相互间的纠纷,即所谓“四姓相犯,皆用汉法”。兴宗时,制定《重熙新定条制》,进一步吸收汉法,如将隋唐五刑中死、流、徒、杖四刑正式纳入刑名。道宗执政时,制定《咸雍条制》,“凡合于《律令》(指《唐律》)者具载之”,采用《唐律》173条。此后,大康年间对《咸雍条制》加以增补时仍以《唐律》为参校依据。
西夏立国后,逐步吸收以唐宋法律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仁宗李仁孝时的《天盛律令》即为典型代表。在立法名称上,西夏以律令作为法典名称,而“律”和“令”是春秋战国以降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律形式。在立法思想上,《天盛律令》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指导,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宗法思想中的“同居相为隐”之制。在立法内容上,《天盛律令》将“八议”“上请”“例减”等列为定制,直接承袭唐宋律法有关内容。
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太宗时,参用辽、宋旧法。熙宗在皇统年间,兼采隋、唐之制,参照辽、宋之法,编成《皇统制》,颁行中外。章宗时,以《唐律疏议》为蓝本,并取《宋刑统》的疏议加以诠释制定《泰和律》,对元代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而言之,辽宋夏金政权虽处在并立纷争的历史时期,但各政权并没有各行其道,反而在交往交流过程中从思想上形成了共尊儒家的理念,在制度上共承了“中国之制”,由此凝聚了华夏认同,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共奉“中国”之号的道路。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